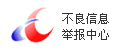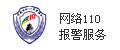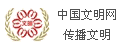【法国】德斯蒙林写给老婆的情书
【法国】德斯蒙林(1762~1794)
德斯蒙林,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主要人物之一,雅各宾派的重要成员之一。参与了雅各宾派的一系列重要活动,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但后来却在革命党的自相残杀中被送上了断头台。
吕西尔是德斯蒙林的妻子,为使丈夫免上断头台,她进行了一系列不懈的努力,这一切非但没有救出丈夫,自己在两周后也被送上了断头台,此信是德斯蒙林在去世前写给妻子的诀别信。
致吕西尔
我的信的附本,也许你还没收到!
酣睡已把我的忧愁驱走了。当一个人走进入梦乡时,他再也没有身陷囹圄的感觉了,他是自由的。上帝对我发了慈悲,在一瞬间之前我还在梦乡中见到你,我接连 地拥抱你、荷拉慈和达龙。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一只眼睛,我看见他的面部缠着一根绷带。我在痛苦面前惊醒了。我发现自己的身上仍锁着铁链,天亮了。我的洛洛 特,我不能再见到你了,不能听你说话了,因为正当你和你母亲在对我说话时,荷拉慈这不知忧虑的孩子叫了声“爸爸,爸爸!”啊,可怕的东西剥夺了我聆听的快 乐,剥夺了我看到你们的快乐,而且剥夺了我获得幸福的快乐。在梦当中和你聚会是我唯一的奢望,也是我唯一的算计。现在既然此路不通,我只得强打精神,至少 想在信中和你多作交谈。我将窗户打开,而那种寂寞之感,和那把你我分离开来的铁栅栏忽然袭入我的脑海,将我的所有心思都给破坏了。我不禁涕泗滂沱,咨嗟叹 息,并且从我的坟墓中向外叫道:“吕西尔,吕西尔,我亲爱的吕西尔,你在何处?你的头从前靠着你的可怜的丈夫,可现在你到哪儿去?你的双臂从前老是抱着 我,使我贴近你,你的双臂此刻在哪里?你的颈项,你的手足,你的美丽的嘴唇,又都在哪里?”啊,昨天,昨天是一种什么样的别离!在我们分别后的每一瞬间, 我觉得我的心灵都已离开了我,到了你的身上,即使是致命的打击也无法让它从你的身体上分离出来。昨天有一阵子,我深感痛苦万分,当我看到你的母亲出现在园 中时,我的心都要碎了。一种本能的力量迫使我走向铁栏,双膝跪下,表示反抗。我把双手合拢,好像是向她(我知道她会不断地对着你叹息)求情。昨天我从她的 手帕上和放下的面纱上看出了她的痛苦,她看到我被逮捕,同样心如刀割。当她再来的时候,请让她靠近你一些,这样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你们,我相信这没有什么 危险..
我在我的小屋子里发现一个缝隙。我将耳朵贴在上面,听到一阵叹息声。我大胆地说了几句话,听到了一个受苦的病人的声音。他问 我的姓名,我如实地告诉了他。“我的天呀!”他这样叫了一声后就跌倒在自己的炕铺上了。接着他又说:“我是德格朗坦。你怎么也到这种地步?反革命达到了顶 点了吗?”我们没敢多谈,一来怕引起胸中的愤恨,在无形中它会驱走心灵上那一点点宁静;二来怕人听见,将我们分开监禁,严加照管。我的爱人,你不懂得什么 是居处于黑暗之中,什么叫做不识事情的真相,什么叫做不加审讯,什么叫做没有半张报纸可看。这就叫做死一般地生存,或者是在棺材里面活着。有人说:问心无 愧便会心安理得,便会有充足的勇气。啊,我的妻,吕西尔,倘若人都是上帝,这种说法可能才是真理!
在这个时候,革命裁判所的委员们来问我是否曾图谋反抗共和国。这是何等地可笑啊!最纯洁的共和主义岂能被诬蔑!我看到了自己,遭遇到什么
样的命运。我的亲爱的吕西尔,我的洛洛特,祝你好,并请代我向父亲请安!写封信给他吧,在我的身上,你已看到了人类野蛮和忘恩的一个例子。你看,我的担 忧是有根据的,我的每一次预言都要应验,可是,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辱没你,我是一个贤妻的好丈夫,还是一个慈父的好儿子,并且又是一个孩子的好爸 爸。我的兄弟们都为共和国而死去了,现在,我要踏着他们的脚印前进。我相信一切正义的、自由的和相信真理的朋友对我会表示敬意和同情。我死了,仅仅32 岁,然而五年以来,我在革命中穿过多少崎岖小道,峭壁悬崖,而仍能活下来,这岂非怪事!..我亲眼见到,几乎一切人都醉心于权力,一切人都和西拉克斯的迪 奥尼斯同声说道:“专制的政权是一种美丽的恩惠。”没有人安慰你的寡妇啊,你应当有点儿称心如意,因为你不幸的丈夫的墓志铭是很荣耀的,那是科托和布洛托 斯的墓志铭,是谋杀专制者的墓志铭!
我的亲爱的吕西尔,我生来就是个诗人,并且生来就是个不幸人的保护者。四年以前,一个生下十个小 孩的母亲找不起律师,我就为她作了辩护,一连忙了好几夜。有一次,我父亲经手的一件大诉讼失败了,我突然出现在今天要杀害我的陪审官们的面前,使审判长惊 讶不已。我知道该怎样用那情至理顺的言辞去打动他们,于是我父亲已经败诉了的案件又被我打赢了。我就是这样一个智者,从未充当过阴谋家。我生来就应该使你 快乐的,生来就应为我们俩,以及你的母亲,我的父亲,以及几个亲密朋友去创造世界的。我所做的梦是圣皮耶尔的梦,我梦想到一个共和国,这是一切人所抱有的 偶像;然而我没想到人类竟是如此无道,如此残酷!因为我的著作当中有些对同志们的戏谑的语言,于是我的功绩被忘却了。我对此实在难以理解。因为这种戏谑, 我和不幸的丹东的友谊被牺牲了,这毋庸讳言。终于我又能和丹东等人一道死去,谢谢我的凶手。我的同志们,我的朋友们,以及“山岳党”全党(除少数人外), 从前曾鼓舞我,向我接吻,和我握手,现在却是畏葸不前,任凭我们陷入困境。那些向我讲过许多道理的人,甚至是那些曾排斥过我的报纸的人,没有一个断言我真 是阴谋家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既然已无法保障,那我们只好以最后的共和主义者的资格去死了。倘若没有断头台,我们也应和科托一样拔剑自刎啊!
1794年4月1日晨5时
德斯蒙林,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主要人物之一,雅各宾派的重要成员之一。参与了雅各宾派的一系列重要活动,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但后来却在革命党的自相残杀中被送上了断头台。
吕西尔是德斯蒙林的妻子,为使丈夫免上断头台,她进行了一系列不懈的努力,这一切非但没有救出丈夫,自己在两周后也被送上了断头台,此信是德斯蒙林在去世前写给妻子的诀别信。
致吕西尔
我的信的附本,也许你还没收到!
酣睡已把我的忧愁驱走了。当一个人走进入梦乡时,他再也没有身陷囹圄的感觉了,他是自由的。上帝对我发了慈悲,在一瞬间之前我还在梦乡中见到你,我接连 地拥抱你、荷拉慈和达龙。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一只眼睛,我看见他的面部缠着一根绷带。我在痛苦面前惊醒了。我发现自己的身上仍锁着铁链,天亮了。我的洛洛 特,我不能再见到你了,不能听你说话了,因为正当你和你母亲在对我说话时,荷拉慈这不知忧虑的孩子叫了声“爸爸,爸爸!”啊,可怕的东西剥夺了我聆听的快 乐,剥夺了我看到你们的快乐,而且剥夺了我获得幸福的快乐。在梦当中和你聚会是我唯一的奢望,也是我唯一的算计。现在既然此路不通,我只得强打精神,至少 想在信中和你多作交谈。我将窗户打开,而那种寂寞之感,和那把你我分离开来的铁栅栏忽然袭入我的脑海,将我的所有心思都给破坏了。我不禁涕泗滂沱,咨嗟叹 息,并且从我的坟墓中向外叫道:“吕西尔,吕西尔,我亲爱的吕西尔,你在何处?你的头从前靠着你的可怜的丈夫,可现在你到哪儿去?你的双臂从前老是抱着 我,使我贴近你,你的双臂此刻在哪里?你的颈项,你的手足,你的美丽的嘴唇,又都在哪里?”啊,昨天,昨天是一种什么样的别离!在我们分别后的每一瞬间, 我觉得我的心灵都已离开了我,到了你的身上,即使是致命的打击也无法让它从你的身体上分离出来。昨天有一阵子,我深感痛苦万分,当我看到你的母亲出现在园 中时,我的心都要碎了。一种本能的力量迫使我走向铁栏,双膝跪下,表示反抗。我把双手合拢,好像是向她(我知道她会不断地对着你叹息)求情。昨天我从她的 手帕上和放下的面纱上看出了她的痛苦,她看到我被逮捕,同样心如刀割。当她再来的时候,请让她靠近你一些,这样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你们,我相信这没有什么 危险..
我在我的小屋子里发现一个缝隙。我将耳朵贴在上面,听到一阵叹息声。我大胆地说了几句话,听到了一个受苦的病人的声音。他问 我的姓名,我如实地告诉了他。“我的天呀!”他这样叫了一声后就跌倒在自己的炕铺上了。接着他又说:“我是德格朗坦。你怎么也到这种地步?反革命达到了顶 点了吗?”我们没敢多谈,一来怕引起胸中的愤恨,在无形中它会驱走心灵上那一点点宁静;二来怕人听见,将我们分开监禁,严加照管。我的爱人,你不懂得什么 是居处于黑暗之中,什么叫做不识事情的真相,什么叫做不加审讯,什么叫做没有半张报纸可看。这就叫做死一般地生存,或者是在棺材里面活着。有人说:问心无 愧便会心安理得,便会有充足的勇气。啊,我的妻,吕西尔,倘若人都是上帝,这种说法可能才是真理!
在这个时候,革命裁判所的委员们来问我是否曾图谋反抗共和国。这是何等地可笑啊!最纯洁的共和主义岂能被诬蔑!我看到了自己,遭遇到什么
样的命运。我的亲爱的吕西尔,我的洛洛特,祝你好,并请代我向父亲请安!写封信给他吧,在我的身上,你已看到了人类野蛮和忘恩的一个例子。你看,我的担 忧是有根据的,我的每一次预言都要应验,可是,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辱没你,我是一个贤妻的好丈夫,还是一个慈父的好儿子,并且又是一个孩子的好爸 爸。我的兄弟们都为共和国而死去了,现在,我要踏着他们的脚印前进。我相信一切正义的、自由的和相信真理的朋友对我会表示敬意和同情。我死了,仅仅32 岁,然而五年以来,我在革命中穿过多少崎岖小道,峭壁悬崖,而仍能活下来,这岂非怪事!..我亲眼见到,几乎一切人都醉心于权力,一切人都和西拉克斯的迪 奥尼斯同声说道:“专制的政权是一种美丽的恩惠。”没有人安慰你的寡妇啊,你应当有点儿称心如意,因为你不幸的丈夫的墓志铭是很荣耀的,那是科托和布洛托 斯的墓志铭,是谋杀专制者的墓志铭!
我的亲爱的吕西尔,我生来就是个诗人,并且生来就是个不幸人的保护者。四年以前,一个生下十个小 孩的母亲找不起律师,我就为她作了辩护,一连忙了好几夜。有一次,我父亲经手的一件大诉讼失败了,我突然出现在今天要杀害我的陪审官们的面前,使审判长惊 讶不已。我知道该怎样用那情至理顺的言辞去打动他们,于是我父亲已经败诉了的案件又被我打赢了。我就是这样一个智者,从未充当过阴谋家。我生来就应该使你 快乐的,生来就应为我们俩,以及你的母亲,我的父亲,以及几个亲密朋友去创造世界的。我所做的梦是圣皮耶尔的梦,我梦想到一个共和国,这是一切人所抱有的 偶像;然而我没想到人类竟是如此无道,如此残酷!因为我的著作当中有些对同志们的戏谑的语言,于是我的功绩被忘却了。我对此实在难以理解。因为这种戏谑, 我和不幸的丹东的友谊被牺牲了,这毋庸讳言。终于我又能和丹东等人一道死去,谢谢我的凶手。我的同志们,我的朋友们,以及“山岳党”全党(除少数人外), 从前曾鼓舞我,向我接吻,和我握手,现在却是畏葸不前,任凭我们陷入困境。那些向我讲过许多道理的人,甚至是那些曾排斥过我的报纸的人,没有一个断言我真 是阴谋家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既然已无法保障,那我们只好以最后的共和主义者的资格去死了。倘若没有断头台,我们也应和科托一样拔剑自刎啊!
1794年4月1日晨5时
上一篇:巴贝夫写给老婆的情书
下一篇:拿破仑写给老婆的情书
名人怎么写情书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