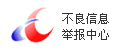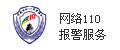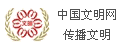【英国】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写给老公的情书
【英国】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888~1923)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英国小说家。出生于新西兰的惠灵顿,是新西兰富商哈罗德爵士 的第三个女儿,毕业于皇家学院。曼斯菲尔德将爱和生命融入她的小说,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很多个年头都被病魔缠身。去世时年仅35岁。著有小说《序曲》、 《在海湾》、《柔弱的心》、《土耳其浴》、《布里尔小姐》等。
致J·M·默利
1915年3月23日
漫步来到巴黎圣母院后面的花园,树上开的白色与粉色的花朵明媚姣丽,于是我在长凳上坐下来。花园正中有一块草坪,还有个大理石雕的水池。麻雀在水中洗 浴,从而溅起喷泉似的水花。白鸽在如茵的绿草上漫步,并不时地整理着羽毛。每条长凳和椅子上都坐着母亲、保姆或老祖父。刚会走路的孩子在用小桶和小铲做泥 饼,或用小篮子来盛栗树的落花,有时还将祖父的帽子扔到了不准游人涉足的草坪上。后来一个中国保姆走来。她穿着绿裤子,黑束腰外衣,头上顶着一顶小头巾 帽,个子矮小,样子滑稽可笑。她坐下来边缝衣服,边鸟似地不停嘴地跟孩子说话,还不时地冲孩子们挤眼,在头发缝里擦针。我良久地注视着这一切,然后突然觉 得我是在梦中。我为什么没有真正的家?不能过真正的生活?为什么我没有中国保姆和两个向我跑来抓住我膝头的孩子?我已不是小姑娘了,我是个女人!我想要这 些东西!什么时候我才能得到这一切!整整一个上午写作。匆忙吃罢中饭下午又写作。然后吃晚饭,吸一支烟,独自一人呆到睡觉时间。爱和欢乐的欲望在胸中荡 漾,难以扼制。而生活却在干涸,象老年妇女乳房中的奶一样在干涸。我要生活,要朋友,要一所房子,要有人在我周围,要花钱,要给予。(亲爱的,只是不给 P.0.银行的存款。)
1915年3月25日
昨天过得不错。文艺女神围成圆圈象波堤切利天宫图顶上的天使一样地 降临了——起码我是这样觉得——我的第一部小说向我张开了双臂,让我扑入它的怀中。我写完了很大一部分,但是首先要抄在薄纸上方能寄给你看。你读过之后也 许会觉得我是在发疯。把你的感想告诉我,好吗?这是篇古怪的作品,我想是春天给了我激情我才这样去写。昨天写作进展不下去,于是停笔到码头去散步。我走了 很远的路,黄昏时出发,夜里之后才回到家中。我散步时路灯亮了,那些小船在跳动。我倚在桥栏上,突然发现其中一只小船正是我心中酝酿的那篇小说的格局—— 规模不大,怪模怪样,或许可以说有点重,憧憧人影在强烈的光线和黑影中移动时给人以怪异的感觉。我还要写明亮的、颤抖的光和哗哗的水声。(这,我的小伙 子,是感情激发的结果)我认为小说写得可以,当然,这不是你所说的那种正规的小说。这个时节春意荡漾,因此我写不出任何严肃的东西。我非常想写一部富有春 的气息的小说。我选定了斯汤达来读。现在每天夜里都读他的作品,一早又读。
1918年1月11日
那封寄自巴黎的激情洋溢的信深深地印人了我的脑海,并且一直在嘲弄着我。我携信去邮寄。天色已暗,寒冷的空气似乎刺透了身体,脚下的地面潮湿极了,两只脚仿佛是两团移动着的烂泥蛇。经过种种麻烦之后,我终于在火车厢内安顿下来(近来在火车上是找不到枕头的)。周围开始喧闹起来。我喜欢同车的人,可是,上帝啊!我全身坐得麻木僵硬,两脚酸疼,熨斗热得几乎要将背部燃烧起来。列车里没有餐车——不可能喝到热的东西。一路上白雪弥漫,直到我们抵达瓦朗斯才停。
我必须承认,乡村在日出时景致美极了,简直太美了。但是我们一点钟才到达马赛。正当我要下车时,一个小流氓冲进车厢想给他的头儿抢座位。他重重地撞了一 下我的胸部,今天还发育呢。我想,毫无疑问,这就是马赛了。我疲惫不堪地拎着行李走了三里路才到了寄存处,这时方才发现去班德尔的火车要在3点30分钟才 发车,于是我决定在站外的小卖部吃点东西。站外的玻璃廊下有不少人,我在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对面坐下。她用眼角上下扫视着我,我觉得奇怪,于是问道:“这 位子有人吗?”“没有,夫人。”她说道,态度傲慢之至,“那边不是还有空桌子吗?我可不愿意你坐在这儿。理由很简单,首先我已经用完午餐,再看着你吃饭会 感恶心,而且,我的胃有点病..”说完,她眉头一抬起身扬长而去。你可以想象得出,这以后我吃了些什么,又想了些什么。
1点30分, 我去登记行李,排队等了一个小时才被告知得先办护照签证然后才能办票。办了签证后,我又去排队,终于在3点整拖着行李上了站台,在人群中直等到4点钟,这 时来了一列火车,然而却驶入另一个站台。人们像猴子爬树似地蜂拥而上。我刚把东西扔上车,就听见有人喊那车是军人专列,在土伦以前不停。真可以!我播摇晃 晃地下了车,上了停在另一站台上的车,一连问了三个人都不知道这趟车是去哪儿的。我象一摊烂泥一样,一头扎进车厢角落里。
和我在一起 的有八个塞尔维亚军官,他们带着两只狗。我是绝对不会去说塞尔维亚人的坏话的。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少女的梦》中的人物那样漂亮——面目俊美、衣着讲究、谈 吐优雅、年轻勇敢、明眸皓齿。但这些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来回奔跑了两个小时,一群士兵和老百姓在车站发生了争执。士兵们非要上车,并让老 百姓全部下车,而且他们态度粗暴,非常可恶,简直可以说无耻之极。他们敲打着车窗,撞开车门,把人们连同行李一古脑地扔出车厢。我们的车厢里涌进了一大群 士兵,他们让那几位塞尔维亚军官也下去。其中有一个人象抓小鸡似的抓住我。我没有说一个字,因为我太疲倦了,只好任凭他摆布。我暗暗告诫自己不要哭叫。这 时一个塞尔维亚军官把那些士兵赶下了车,并说我是他的妻子,与他一起旅行已经五天了。当车站军管负责人来查询时,他仍旧这样说,并把他也赶下了车。随后, 他砰地一声关上门,松开了拴狗的绳子,紧紧地把住门。其他人便挤在联结车厢的门边,而我们就在这四面重围下一直熬到7点钟,这时火车启程了。你真应该听一 听那乒乒乓乓的关门声和吵闹声。他们把窗帘用针别在一起,我在里面一直藏到开车。这时,天色一片漆黑,我心里琢磨着,这下可无法搞清到哪站了。窗外北风呼 呼地嚎叫着,听不见所喊的站名,可是每到一站,他们就拉下窗户,用生硬的法语大声问站。他们都是好小伙儿——很好的小伙子,我不会忘记他们的。9点钟到达 班德尔,我觉得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但我还是抓住了两个军官,在他们的协助下跌跌撞撞地过了铁道。我是无论如何无法自己单独行走了,幸好德班思旅馆的 服务员在车站。尽管他说,“旅馆不好,因为经理不好,”他还是带我到了旅馆。进了旅馆,大厅里很冷而且烟雾缭绕。一个陌生的女人走了出来,边走边用餐巾擦着嘴。我马上意识到旅馆的主人换了。她说她没收到什么信,但旅馆里有的是房间。随后她领我去看房子。我预订的房间已被人占了,只好选了隔壁的 房间,条件是把屋内的两张床搬走一张。这是最便宜的住房,每天十二法郎!其它的房间装有自来水,每天十三法郎!门厅里的大炉子没有生火..我要来了热水、 热水瓶,喝过了汤,然后将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眼睛。用我自带的杯子喝了点白兰地,就倒在床上。折腾了半天应该好好睡一觉,无暇回顾发生的事了..
早晨我打开窗帘,外面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我在床上一直呆到吃午饭的时候。我的大件行李到了,于是我起了床。午饭后又到城里转了转。梅那德一家人暂时搬 走了,卖烟草的女人认不出我,也没有烟草可卖了。这里没有一个人记得我。我买了些书写用品和一些硬糖块(约一分钱两块)。突然间碰上了加莫尔夫人,她开始 也没认出我宋,是我告诉她我是谁的。她十分和善。“啊,你变化很大,那会儿你病得很重,是吧?你现在不像以前那样了。”我跟她一起去了小商店(与原来一模 一样),看到了那样热心肠的老妈妈。我买了一小瓶樱桃酱,返回旅馆后发现房间还未收拾。
亲爱的,你可以想像得到,我十分沮丧。经过了 长途跋涉后,直到现在我还未恢复体力,但是我会慢慢好起来的。一旦我有了力量就会安排好一切。尽管我两眼茫茫,然而此地的美景依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阳光 下万物放射着夺目的光彩,周围是紫蓝色的大海。芭蕉叶在阳光下闪亮,峦峰叠翠美不胜收。阴影中显现的是紫色,而光明处却是玉一般的碧绿。窗外的含羞草已结 出花蕾。不要为我担心,既然已度过了那段旅程,以及巴黎的冰雪,我绝不会在中途跌倒。房间一经收拾完毕,我就着手工作。我的确是这样感觉的,这也是最为重 要的。尽管这一段确实有些乱,但我还不至于狼狈不堪。我要把我的真实感觉全告诉你,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只苍蝇、掉进了牛奶杯里又被捞了出来,浑身上下浸透了 牛奶,正在晾干。信要很长时间才能到——大概六至八天,所以收不到信时不要担心。
你自己要多保重,像我爱你一样地爱我吧。唉,今天不是写这些的时候,因为我的胸部又开始疼了。我的双臂飞向你,拥抱你。我需要你。我很孤单,而且还有点晕,但这只是暂时的。
四
1918年5月17日
安和德雷那会儿在利斯克德。安正像我想象的,晒黑的皮肤,浅色的海螺形眼睛,背着一个很大的、鼓鼓囊羹的白包,里面装着她的水瓶、德雷的背心、一盒油 彩、一把野花,还有一个“最最漂亮的柠檬”。德雷十分和蔼:他把一切事都干了。我们轻松愉快地上了路,去芦港。天气很热——一切都灼热而又宁静,只有鸟儿 在高声歌唱,风铃草散发出蜜般的醇香。一路上的经历大令人惊奇了,既不是英国式的,也不是法国式或德国式的。我还是慢慢讲吧。旅馆差来轻便马车接我们上 路,驾车的是一个白头发、很有个性的男孩子,他驾驭着马就像是在摆布一条凶悍暴躁的白龙——有意要让我们看看他的本事嘛。我们驱车穿过大街小巷,一条条街 巷仿佛是连在一起的花环,下方是大海,海面上飞翔着海鸥——有的海鸥落在屋顶上用嘴梳理着自己的羽毛,这花环似的街道和大海一直送我们到了旅馆,旅馆面对 大海,座落在花园里。再没有比这更令人神往的地方了。旅馆是大型的,“完全一流水平”——价格昂贵得吓人。旅馆里有一座全玻璃墙庭园,天气不好时就可以去 那
儿,里面设有长椅,像一个大走廊,整个庭园既向阳又临海。安为我订了一套极其宽敞的房间,三个窗户全部向南。一清早,阳光就洒满房 间,到下午三点阳光才渐渐退去。房间整洁、豁亮,屋内有一把很深的扶手椅,一张双层垫子的软床——走廊那边是一间一流水平的浴室,全天供应热水,厕所也非 常高级,和浴室加起来可以成为半个疗养院..现在十点,我要睡觉了。我的房前全部是大海,现在百叶窗已放下,那过去所熟悉的声音又漂浮进来,让我感到很悲 伤。我不禁觉得我们近来的生活是多么盲目、可怕,总象是丢失了什么再去寻找什么,这中间黄金般的时刻有几回?休息的机会有多少?但我不用渡海过去了,你会 过来度假的——就是下个月。离开你真是痛苦,一切都听天由命吧。原谅我,如果我曾经——曾经怎么样了——我忘记了。我发现生病是多么令人难以接受啊。但 是,唉,倘若你真能明白我是多么地爱你..
五
1919年11月3日
稍晚。L·M·带着你星 期四寄来的信刚刚回来,里面附有哈代的原信。你能把它给我,我欣喜万分。这可是件珍品。这种情形有多奇怪:一个人到死的时候,他的诗才得到承认!人能做到 这一点是多么伟大!跟我们这些不断渴望着生活中的兴奋高潮的急躁生灵来说是多么不同!生活啊!生活!我们呼喊。而哈代却以如此冷静的笔触描写,好像他正驶 进一个平静的港湾,船帆卷起,随着悠悠的潮水漂入。你把那些东西不加修改原封不动地给了他,这很好。我肯定,他会深刻理解你的,但他毕竟年事已高、历尽沧 桑。由于年龄和漫长的经历,他期待着死神的降临。
我能想像你把这一切有关细节都写信给下一代的一个青年,只是不会告诉他,你的妻子死后不要修墓,而只要一只蝴蝶在她的坟上翩飞而过。
六
1919年11月8日
..同以往一样,我想一切会如愿以偿——美满、幸福,没有对疾病的恐惧(疾病是可怕的),与L·M·和睦相处,有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我真是个傻瓜!在 所有这些之中,病的痊愈才真正重要,有了它就足够了,其它的以后再说。当然要工作,工作是第二生命。当你谈到种一棵希望之树时,我感到——噢,是你在这样 讲。种吧——种上一棵希望之树,亲爱的,我不会去动摇它。让我坐在树下仰望它,让那浓密的枝叶覆盖我。你要常到那儿去看我,我们紧紧地拥抱着抬头寻觅树枝 间的花蕾和花朵。不,世间根本没有什么上帝。很奇怪,今天早晨我却想说:“上帝保佑你!”或者“上天护卫我们!”后来,我想到了神灵,可他们都是些鼻子残 缺的大理石雕像。世上本来就不存在什么上帝、天堂或任何救世主,有的只是爱。大概爱是法力无边的。“嗨,我把爱奉作我的神灵。”这是谁说的?真是妙极了。
七
1920年11月7日
亲吻是件奇怪的事情。刚刚我站在一棵树下,树上落下的精美的金黄色叶子洒满了花园的小路。忽然,一片叶子极轻盈地向我飘来。立刻,我们相互亲吻了。透过银色的枝权看得见湛蓝的天空..像蓝宝石一样。
我认为到时候了,到我们稍稍互诉衷情的时候了。我们可曾有过时间站在树下倾诉自己的爱慕之情?可曾有过时间坐在海边互相为对方编制花环?
茶玫瑰开了,你知道茶玫瑰那奇异、优雅的香味吗?它的花苞在绽开时与其它玫瑰是那样不同,它的刺红得那么深,叶子几乎是紫色的,这些你都知道吗?
我想玛丽从市场上买回家的一定是桔花。我把带长枝的都插进罐子里,剩下的小权放在浅底的玻璃碗里了。房子里飘溢着花香,好象土耳其君主在等待他最年轻的 新娘初次到来似的。玛丽走过来唱了一会儿歌,就像给在山里找到的野仙客来唱圣歌一样。我家乡的小紫罗兰生长得那么茂盛,人们禁不住前往观赏。
如果我活得更长一些,就变成月桂树丛,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没有人迎接你,迎接你的只是一朵茉莉花。也许这是每天上午接受日光照晒的结果,而且从来役误过。一张黑纸扇像是女士唯一的穿戴。不过你一定要到这儿来,到南方住住,忘掉灰暗。这儿是神圣的——不次于..
八
1922年11月2日
上次给你写信之后,非常生自己的气。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为自己感到羞耻。但是你是了解我的,所以会理解这一切。我总是不实际,认为一切都能够改变,一切都能在一瞬间得到更新。你我都很难做到不“热烈”,而当我热烈起来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我又有几分虚假..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英国小说家。出生于新西兰的惠灵顿,是新西兰富商哈罗德爵士 的第三个女儿,毕业于皇家学院。曼斯菲尔德将爱和生命融入她的小说,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很多个年头都被病魔缠身。去世时年仅35岁。著有小说《序曲》、 《在海湾》、《柔弱的心》、《土耳其浴》、《布里尔小姐》等。
致J·M·默利
1915年3月23日
漫步来到巴黎圣母院后面的花园,树上开的白色与粉色的花朵明媚姣丽,于是我在长凳上坐下来。花园正中有一块草坪,还有个大理石雕的水池。麻雀在水中洗 浴,从而溅起喷泉似的水花。白鸽在如茵的绿草上漫步,并不时地整理着羽毛。每条长凳和椅子上都坐着母亲、保姆或老祖父。刚会走路的孩子在用小桶和小铲做泥 饼,或用小篮子来盛栗树的落花,有时还将祖父的帽子扔到了不准游人涉足的草坪上。后来一个中国保姆走来。她穿着绿裤子,黑束腰外衣,头上顶着一顶小头巾 帽,个子矮小,样子滑稽可笑。她坐下来边缝衣服,边鸟似地不停嘴地跟孩子说话,还不时地冲孩子们挤眼,在头发缝里擦针。我良久地注视着这一切,然后突然觉 得我是在梦中。我为什么没有真正的家?不能过真正的生活?为什么我没有中国保姆和两个向我跑来抓住我膝头的孩子?我已不是小姑娘了,我是个女人!我想要这 些东西!什么时候我才能得到这一切!整整一个上午写作。匆忙吃罢中饭下午又写作。然后吃晚饭,吸一支烟,独自一人呆到睡觉时间。爱和欢乐的欲望在胸中荡 漾,难以扼制。而生活却在干涸,象老年妇女乳房中的奶一样在干涸。我要生活,要朋友,要一所房子,要有人在我周围,要花钱,要给予。(亲爱的,只是不给 P.0.银行的存款。)
1915年3月25日
昨天过得不错。文艺女神围成圆圈象波堤切利天宫图顶上的天使一样地 降临了——起码我是这样觉得——我的第一部小说向我张开了双臂,让我扑入它的怀中。我写完了很大一部分,但是首先要抄在薄纸上方能寄给你看。你读过之后也 许会觉得我是在发疯。把你的感想告诉我,好吗?这是篇古怪的作品,我想是春天给了我激情我才这样去写。昨天写作进展不下去,于是停笔到码头去散步。我走了 很远的路,黄昏时出发,夜里之后才回到家中。我散步时路灯亮了,那些小船在跳动。我倚在桥栏上,突然发现其中一只小船正是我心中酝酿的那篇小说的格局—— 规模不大,怪模怪样,或许可以说有点重,憧憧人影在强烈的光线和黑影中移动时给人以怪异的感觉。我还要写明亮的、颤抖的光和哗哗的水声。(这,我的小伙 子,是感情激发的结果)我认为小说写得可以,当然,这不是你所说的那种正规的小说。这个时节春意荡漾,因此我写不出任何严肃的东西。我非常想写一部富有春 的气息的小说。我选定了斯汤达来读。现在每天夜里都读他的作品,一早又读。
1918年1月11日
那封寄自巴黎的激情洋溢的信深深地印人了我的脑海,并且一直在嘲弄着我。我携信去邮寄。天色已暗,寒冷的空气似乎刺透了身体,脚下的地面潮湿极了,两只脚仿佛是两团移动着的烂泥蛇。经过种种麻烦之后,我终于在火车厢内安顿下来(近来在火车上是找不到枕头的)。周围开始喧闹起来。我喜欢同车的人,可是,上帝啊!我全身坐得麻木僵硬,两脚酸疼,熨斗热得几乎要将背部燃烧起来。列车里没有餐车——不可能喝到热的东西。一路上白雪弥漫,直到我们抵达瓦朗斯才停。
我必须承认,乡村在日出时景致美极了,简直太美了。但是我们一点钟才到达马赛。正当我要下车时,一个小流氓冲进车厢想给他的头儿抢座位。他重重地撞了一 下我的胸部,今天还发育呢。我想,毫无疑问,这就是马赛了。我疲惫不堪地拎着行李走了三里路才到了寄存处,这时方才发现去班德尔的火车要在3点30分钟才 发车,于是我决定在站外的小卖部吃点东西。站外的玻璃廊下有不少人,我在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对面坐下。她用眼角上下扫视着我,我觉得奇怪,于是问道:“这 位子有人吗?”“没有,夫人。”她说道,态度傲慢之至,“那边不是还有空桌子吗?我可不愿意你坐在这儿。理由很简单,首先我已经用完午餐,再看着你吃饭会 感恶心,而且,我的胃有点病..”说完,她眉头一抬起身扬长而去。你可以想象得出,这以后我吃了些什么,又想了些什么。
1点30分, 我去登记行李,排队等了一个小时才被告知得先办护照签证然后才能办票。办了签证后,我又去排队,终于在3点整拖着行李上了站台,在人群中直等到4点钟,这 时来了一列火车,然而却驶入另一个站台。人们像猴子爬树似地蜂拥而上。我刚把东西扔上车,就听见有人喊那车是军人专列,在土伦以前不停。真可以!我播摇晃 晃地下了车,上了停在另一站台上的车,一连问了三个人都不知道这趟车是去哪儿的。我象一摊烂泥一样,一头扎进车厢角落里。
和我在一起 的有八个塞尔维亚军官,他们带着两只狗。我是绝对不会去说塞尔维亚人的坏话的。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少女的梦》中的人物那样漂亮——面目俊美、衣着讲究、谈 吐优雅、年轻勇敢、明眸皓齿。但这些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来回奔跑了两个小时,一群士兵和老百姓在车站发生了争执。士兵们非要上车,并让老 百姓全部下车,而且他们态度粗暴,非常可恶,简直可以说无耻之极。他们敲打着车窗,撞开车门,把人们连同行李一古脑地扔出车厢。我们的车厢里涌进了一大群 士兵,他们让那几位塞尔维亚军官也下去。其中有一个人象抓小鸡似的抓住我。我没有说一个字,因为我太疲倦了,只好任凭他摆布。我暗暗告诫自己不要哭叫。这 时一个塞尔维亚军官把那些士兵赶下了车,并说我是他的妻子,与他一起旅行已经五天了。当车站军管负责人来查询时,他仍旧这样说,并把他也赶下了车。随后, 他砰地一声关上门,松开了拴狗的绳子,紧紧地把住门。其他人便挤在联结车厢的门边,而我们就在这四面重围下一直熬到7点钟,这时火车启程了。你真应该听一 听那乒乒乓乓的关门声和吵闹声。他们把窗帘用针别在一起,我在里面一直藏到开车。这时,天色一片漆黑,我心里琢磨着,这下可无法搞清到哪站了。窗外北风呼 呼地嚎叫着,听不见所喊的站名,可是每到一站,他们就拉下窗户,用生硬的法语大声问站。他们都是好小伙儿——很好的小伙子,我不会忘记他们的。9点钟到达 班德尔,我觉得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但我还是抓住了两个军官,在他们的协助下跌跌撞撞地过了铁道。我是无论如何无法自己单独行走了,幸好德班思旅馆的 服务员在车站。尽管他说,“旅馆不好,因为经理不好,”他还是带我到了旅馆。进了旅馆,大厅里很冷而且烟雾缭绕。一个陌生的女人走了出来,边走边用餐巾擦着嘴。我马上意识到旅馆的主人换了。她说她没收到什么信,但旅馆里有的是房间。随后她领我去看房子。我预订的房间已被人占了,只好选了隔壁的 房间,条件是把屋内的两张床搬走一张。这是最便宜的住房,每天十二法郎!其它的房间装有自来水,每天十三法郎!门厅里的大炉子没有生火..我要来了热水、 热水瓶,喝过了汤,然后将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眼睛。用我自带的杯子喝了点白兰地,就倒在床上。折腾了半天应该好好睡一觉,无暇回顾发生的事了..
早晨我打开窗帘,外面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我在床上一直呆到吃午饭的时候。我的大件行李到了,于是我起了床。午饭后又到城里转了转。梅那德一家人暂时搬 走了,卖烟草的女人认不出我,也没有烟草可卖了。这里没有一个人记得我。我买了些书写用品和一些硬糖块(约一分钱两块)。突然间碰上了加莫尔夫人,她开始 也没认出我宋,是我告诉她我是谁的。她十分和善。“啊,你变化很大,那会儿你病得很重,是吧?你现在不像以前那样了。”我跟她一起去了小商店(与原来一模 一样),看到了那样热心肠的老妈妈。我买了一小瓶樱桃酱,返回旅馆后发现房间还未收拾。
亲爱的,你可以想像得到,我十分沮丧。经过了 长途跋涉后,直到现在我还未恢复体力,但是我会慢慢好起来的。一旦我有了力量就会安排好一切。尽管我两眼茫茫,然而此地的美景依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阳光 下万物放射着夺目的光彩,周围是紫蓝色的大海。芭蕉叶在阳光下闪亮,峦峰叠翠美不胜收。阴影中显现的是紫色,而光明处却是玉一般的碧绿。窗外的含羞草已结 出花蕾。不要为我担心,既然已度过了那段旅程,以及巴黎的冰雪,我绝不会在中途跌倒。房间一经收拾完毕,我就着手工作。我的确是这样感觉的,这也是最为重 要的。尽管这一段确实有些乱,但我还不至于狼狈不堪。我要把我的真实感觉全告诉你,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只苍蝇、掉进了牛奶杯里又被捞了出来,浑身上下浸透了 牛奶,正在晾干。信要很长时间才能到——大概六至八天,所以收不到信时不要担心。
你自己要多保重,像我爱你一样地爱我吧。唉,今天不是写这些的时候,因为我的胸部又开始疼了。我的双臂飞向你,拥抱你。我需要你。我很孤单,而且还有点晕,但这只是暂时的。
四
1918年5月17日
安和德雷那会儿在利斯克德。安正像我想象的,晒黑的皮肤,浅色的海螺形眼睛,背着一个很大的、鼓鼓囊羹的白包,里面装着她的水瓶、德雷的背心、一盒油 彩、一把野花,还有一个“最最漂亮的柠檬”。德雷十分和蔼:他把一切事都干了。我们轻松愉快地上了路,去芦港。天气很热——一切都灼热而又宁静,只有鸟儿 在高声歌唱,风铃草散发出蜜般的醇香。一路上的经历大令人惊奇了,既不是英国式的,也不是法国式或德国式的。我还是慢慢讲吧。旅馆差来轻便马车接我们上 路,驾车的是一个白头发、很有个性的男孩子,他驾驭着马就像是在摆布一条凶悍暴躁的白龙——有意要让我们看看他的本事嘛。我们驱车穿过大街小巷,一条条街 巷仿佛是连在一起的花环,下方是大海,海面上飞翔着海鸥——有的海鸥落在屋顶上用嘴梳理着自己的羽毛,这花环似的街道和大海一直送我们到了旅馆,旅馆面对 大海,座落在花园里。再没有比这更令人神往的地方了。旅馆是大型的,“完全一流水平”——价格昂贵得吓人。旅馆里有一座全玻璃墙庭园,天气不好时就可以去 那
儿,里面设有长椅,像一个大走廊,整个庭园既向阳又临海。安为我订了一套极其宽敞的房间,三个窗户全部向南。一清早,阳光就洒满房 间,到下午三点阳光才渐渐退去。房间整洁、豁亮,屋内有一把很深的扶手椅,一张双层垫子的软床——走廊那边是一间一流水平的浴室,全天供应热水,厕所也非 常高级,和浴室加起来可以成为半个疗养院..现在十点,我要睡觉了。我的房前全部是大海,现在百叶窗已放下,那过去所熟悉的声音又漂浮进来,让我感到很悲 伤。我不禁觉得我们近来的生活是多么盲目、可怕,总象是丢失了什么再去寻找什么,这中间黄金般的时刻有几回?休息的机会有多少?但我不用渡海过去了,你会 过来度假的——就是下个月。离开你真是痛苦,一切都听天由命吧。原谅我,如果我曾经——曾经怎么样了——我忘记了。我发现生病是多么令人难以接受啊。但 是,唉,倘若你真能明白我是多么地爱你..
五
1919年11月3日
稍晚。L·M·带着你星 期四寄来的信刚刚回来,里面附有哈代的原信。你能把它给我,我欣喜万分。这可是件珍品。这种情形有多奇怪:一个人到死的时候,他的诗才得到承认!人能做到 这一点是多么伟大!跟我们这些不断渴望着生活中的兴奋高潮的急躁生灵来说是多么不同!生活啊!生活!我们呼喊。而哈代却以如此冷静的笔触描写,好像他正驶 进一个平静的港湾,船帆卷起,随着悠悠的潮水漂入。你把那些东西不加修改原封不动地给了他,这很好。我肯定,他会深刻理解你的,但他毕竟年事已高、历尽沧 桑。由于年龄和漫长的经历,他期待着死神的降临。
我能想像你把这一切有关细节都写信给下一代的一个青年,只是不会告诉他,你的妻子死后不要修墓,而只要一只蝴蝶在她的坟上翩飞而过。
六
1919年11月8日
..同以往一样,我想一切会如愿以偿——美满、幸福,没有对疾病的恐惧(疾病是可怕的),与L·M·和睦相处,有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我真是个傻瓜!在 所有这些之中,病的痊愈才真正重要,有了它就足够了,其它的以后再说。当然要工作,工作是第二生命。当你谈到种一棵希望之树时,我感到——噢,是你在这样 讲。种吧——种上一棵希望之树,亲爱的,我不会去动摇它。让我坐在树下仰望它,让那浓密的枝叶覆盖我。你要常到那儿去看我,我们紧紧地拥抱着抬头寻觅树枝 间的花蕾和花朵。不,世间根本没有什么上帝。很奇怪,今天早晨我却想说:“上帝保佑你!”或者“上天护卫我们!”后来,我想到了神灵,可他们都是些鼻子残 缺的大理石雕像。世上本来就不存在什么上帝、天堂或任何救世主,有的只是爱。大概爱是法力无边的。“嗨,我把爱奉作我的神灵。”这是谁说的?真是妙极了。
七
1920年11月7日
亲吻是件奇怪的事情。刚刚我站在一棵树下,树上落下的精美的金黄色叶子洒满了花园的小路。忽然,一片叶子极轻盈地向我飘来。立刻,我们相互亲吻了。透过银色的枝权看得见湛蓝的天空..像蓝宝石一样。
我认为到时候了,到我们稍稍互诉衷情的时候了。我们可曾有过时间站在树下倾诉自己的爱慕之情?可曾有过时间坐在海边互相为对方编制花环?
茶玫瑰开了,你知道茶玫瑰那奇异、优雅的香味吗?它的花苞在绽开时与其它玫瑰是那样不同,它的刺红得那么深,叶子几乎是紫色的,这些你都知道吗?
我想玛丽从市场上买回家的一定是桔花。我把带长枝的都插进罐子里,剩下的小权放在浅底的玻璃碗里了。房子里飘溢着花香,好象土耳其君主在等待他最年轻的 新娘初次到来似的。玛丽走过来唱了一会儿歌,就像给在山里找到的野仙客来唱圣歌一样。我家乡的小紫罗兰生长得那么茂盛,人们禁不住前往观赏。
如果我活得更长一些,就变成月桂树丛,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没有人迎接你,迎接你的只是一朵茉莉花。也许这是每天上午接受日光照晒的结果,而且从来役误过。一张黑纸扇像是女士唯一的穿戴。不过你一定要到这儿来,到南方住住,忘掉灰暗。这儿是神圣的——不次于..
八
1922年11月2日
上次给你写信之后,非常生自己的气。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为自己感到羞耻。但是你是了解我的,所以会理解这一切。我总是不实际,认为一切都能够改变,一切都能在一瞬间得到更新。你我都很难做到不“热烈”,而当我热烈起来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我又有几分虚假..
上一篇:斯维尔德洛夫写给老婆的情书
下一篇:李普曼写给老婆的情书
名人怎么写情书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